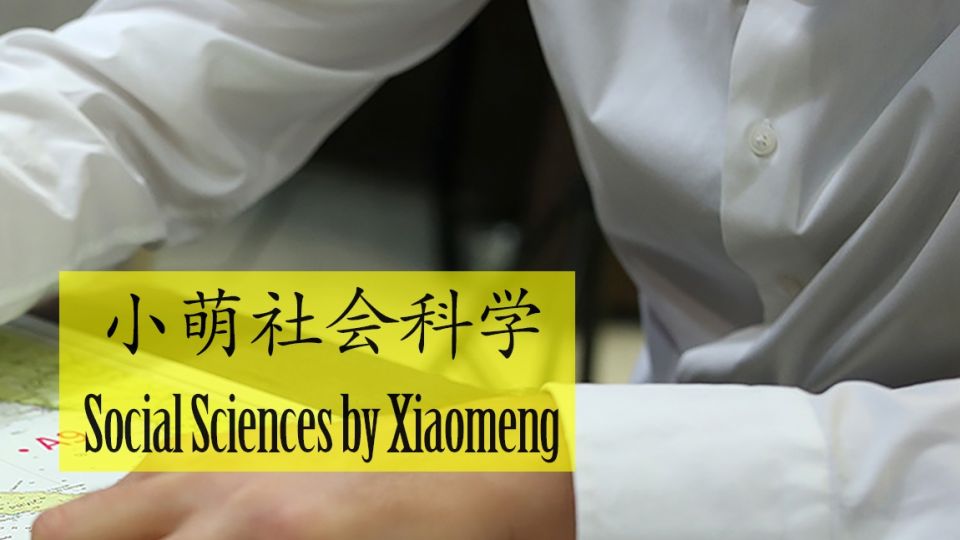吴小萌
(六)
春秋战国,百家争鸣;春秋之后,多家消亡,儒道犹存。
消亡的多家中,有个墨家。
大家都知道,墨家的思想宗旨,是为底层老百姓服务的;与之相反的是,大家都认为,儒家的思想,则是全然为了统治阶层。所以,鲁迅称赞墨子一类的人,“是中国的脊梁”;胡适称墨子“也许是中国出现的最伟大的人物”;毛泽东感叹墨子“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”(注意,毛泽东是不大赞扬古代“圣人”的)。
一个理论,单单凭它只为老百姓服务,就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吗?
墨子的为人民(孟子也是为人民的,但那是另外的一种为人民,不在这里探讨),是只单单看到了人民呢,还是他把人民和统治者一起都给关照了?似乎不是!
孔子的为统治阶级(道家也是为统治阶级的,但又是另一种的为统治阶级),是只单单为了统治阶级呢,还是连带着把人民也给一起“服务”了?好像是的!
我们不能单纯地看一个理论是在为哪一群人服务,为君王还是为百姓;我们要审视的是,如果一个理论不存在基本的社会自洽,那它能起到为“整个社会”这个复杂体系服务的作用吗?
墨家主张人人平等(兼爱),但等到遇到问题时,等到各有各的意见争持不下时,墨子最后说:“一定需要有一个人来定夺”,也就是说,让他来最终说了算。但这样一来,就不是人人平等了!于是,墨家理论的不自洽,就显现了。
墨家的理论,反对社会分成阶级,反对儒家的由不同等级引发的社会“互动模式”,反对孔子的由近及远的、有差等的“仁爱”。墨家提倡的是广泛的、不分你我的、不分家里外头的“兼爱”(从这里,是不是隐约看到了毛泽东对家人的态度呢?)。
然而,有个问题,墨家的这种非阶梯式的、平板状的社会,由谁来领导呢?系统再扁平,总不能没有领导吧?好吧,墨家说,由一个极特殊的人物来领导,他们把他叫做“巨子”(故称“鉅子”,金字旁,跟墨家的善于用兵打仗有关)。
形式上,墨家也认可社会等级(否则,就连国君也不能承认了),但那只是名义上的等级,而没有实际的实惠。墨家认为,社会等级,不应该是赚取实惠的工具,包括巨子本身在内,也不允许他有超越常人的实惠。这种实惠包括物质的,也包括意识形态的。也就是说,在物质上,大家,包括我巨子在内,我们都一样,共同奋斗,共同致富,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公有化;在意识形态上,在思想上,大家,也包括我巨子在内,我们完全步调一致,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。
于是,有人弱弱地问,说,物质均等,容易实现,因为物质是看得见的,一旦你多得了,我少得了,大家都看得见,你分给我一点,不就平衡了嘛!意识形态均等,肿么实现呢?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,肿么办呢?你说往东,我偏要往西,最后听谁的呢?
巨子说,行了,别争了,意识形态,最后听我的!
于是,墨子的理论格局,就此形成,理论的不自洽,也蕴藏之中。
(七)
影影绰绰地,我们在墨子身上,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子,也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核。
但是,马克思的理论是基本自洽的,它虽然也为民众,但它的领导者是一个政党,它内含西方资本主义相互制约的传统,它有内部的反馈机制,它有历史与未来。而毛泽东思想就不然了,它的领导者虽然形式上也是政党,形式上也有民主集中,但实际的上下级关系,则沦为了众人与“巨子”样的关系。
奇怪的是,当我们回顾党史的时候,当中国共产党早期节节失利的时候,我们的领导层,是一个内部充满制约和反馈的政党;但当我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,最终战胜国民党“反动派”的时候,我们的领导,却是个“巨子”,并且,一直到毛泽东离开人世,其“巨子”的地位,不大有人敢撼动,也没有被人撼动过。
毛泽东思想,是介于马克思主义和墨家理论之间的一个特殊模型,是一个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结合的模型,它有一个“高大上”的名头,却行使着一个古老的“狭义”作风,它有为底层大众谋福利的初衷,却继承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古老传统。
毛泽东思想的不自洽,没能损害军事指挥上的胜利,但却深深重创了中华民族30年的经济发展进程。
不能说毛泽东没有意识到经济系统的复杂性(《论十大关系》),但他的墨家情怀的简单,没能使他看到复杂系统的内禀自发的规律,而是必然地采用了“国家计划控制”这样的单一“凯恩斯”式方法论,来对这个社会经济展开一种“巨子”统帅下的线性管理的实践运动。
当有人要全面修正毛泽东思想的时候,“巨子”发威,反动了文化大革命。
(八)
某个理论,一定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吗?
不能!任何理论都有其边界,任何话语都有其语境。边界、语境,可以是空间,可以是时间,可以是民族,也可以是人群。
墨子的理论,也有它得以生效的范围。
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,在特定的范畴内,对特定的人群,墨子理论会起作用。它在春秋战国时起过作用,它在中国的“新民主主义革命”时期,通过毛泽东的努力,也起过作用。有理由相信,它在现代和未来的军事管理中,还会继续起作用。
然而,当我们把视野一放大,从局部放大到全局,从一个人对一群人的发号施令,放大到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前后左右关系,墨子理论的不适用就立刻凸现出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,纵观中国历史,自秦汉开始,墨子理论便销声匿迹,没有被主流社会所采纳的根本原因。
我们学数学,首先是从整数开始的。
给你一筐苹果,让你用整数把一筐苹果给数出来,没有丝毫问题。但如果我问,半个苹果如何数?1/3个苹果又如何数?或问,某个较大的苹果比某个较小的苹果大百分之多少?这时,整数的理论,就无能为力了。
为了回答如何数半个苹果的问题,人们发明了分数和百分数。
人类是为了解决各种“半个苹果”的问题,才被迫一步一步地扩展了数的概念的。从整数、分数、有理数,再到无理数,人类填满了数轴上的点;当数轴不够用时,人类又把触角延伸到了数轴以外,去探寻实数以外的虚数空间。人类扩展数的概念的目的,无非是要用“不同边界的数”,来更有效地诠释不同边界的世界。
在我们切开苹果的时候,或我们要比较两个苹果哪个大、哪个小的时候,整数黯然失色,而分数和百分数,则粉墨登场。
反过来,当我们仅仅需要清点一筐苹果的个数的时候,你拿出分数和无理数来说事,是不是在故意搅和呢?
当需要社会成员组成铁板一块的时候,你拿儒家和道家来搅和,就如同你拿无理数来清点苹果。相反,当我们面对由复杂的人群组成的复杂经济社会的时候,如果我们不用内含反馈机制的、非线性的思维来分析的话,而仍然只拿相对单纯的、不自洽的墨家理论来指导实践,当然也就注定了要失败。
量子力学,超越了牛顿经典力学,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仍然用牛顿定律来处理日常生活;而只有当我们探讨光子的波粒二象性的时候,我们才使用量子力学。
于是,我们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。当年的毛泽东,凭借着对马克思的懵懂理解,继承了墨家的衣钵,打着“兼爱”和“均等”的旗号,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,安抚和号召起广大的农工,终于打败了以“完备儒家理论”和“中国资本主义”为基石的蒋介石政体。
(九)
马克思 /韦伯,和卡尔 /马克思,同样都是德国人,同样叫“马克思”,但马克思是姓马克思,韦伯是名字叫马克思。
韦伯从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出发,看到了贪欲与克制的互相制约,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基督教国家繁荣的内在根据。
而中国古老的孔子模式,其实同样拥有这种正反两方面的基因。孔子说,“克己复礼”和“过犹不及”,这种“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”的灵动思维,指导着中华民族,曾几番走过辉煌的盛世。
孟子是孔子的一种进化,强调了“性本善”,提出了超越动物性的“几希”人性和人性的“四端”;墨子脱离了儒家,眼光从大社会下沉到人民大众,强调“大同”和军事服从。孟子和墨子,是否总让人觉得,他们偏颇了一极,消减了另一极呢?
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人的自由解放,与以往不同,是在阶级斗争的语境下呈现的。而当“锁链”被砸碎后,在共产主义共同分配的理想下,追求自由的动力就不见了。当20世纪60年代,西方的青年学生,走上街头,打着马克思理论的旗号,再次追求新一轮的自由解放时,那已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的异向解读了。
引入正反方向的辩证和反馈,是往复杂方向迈进了一大步。
但是,当今世界,我们却很难继续地迈出另一大步。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所有人们,正在为是否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降的既定规则的“遵守”或“反叛”,和对未来世界的“确定”或“不确定”,集体陷入纠结。
世界,已经从资本主义的“现代”顶端往下“坠落”,伴随着上述提到的那场学生运动,伴随着女权主义、性解放、艺术的现代化(即艺术的后现代)、建筑的解构主义,伴随着教皇对进化论的承认、经济的全球化和移民浪潮之后的矛盾、世界格局的多元化和对生态圈环保的关注,更伴随着恐怖主义的兴起、文化冲突的升级,以及网络语言个性化的快速演进,等等、等等,伴随着所有的对以往“规则”的挑战,世界进入了“后现代”模式。
说是“后现代”,但对中国人来讲,这个“后现代”并不陌生。 两千多年前,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,就是对那个稳固的西周“现代”社会模式的“后现代”怀疑和反叛。
这样看来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,经济建设氛围下的经济活动和人的思想状态,相对于已成为“既定方针”的毛泽东思想,是不是就应该表现出一种对规则的怀疑和不适应呢?
目光转向当代中国,在这块独特的东方地域上,凭借着深重的文化背景的传承,在思考当今中国社会该走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,面对西方启蒙运动所确立的“民主”政体和资本主义模式的“成功规则”的双重施压,是不是也应该本着“后现代”的精神,自信而智慧地说“不!”呢?
在是否遵循“西方”一元主义的纠结中,另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吵也从未停歇,那就是对未来愿景的选择、和所选择的愿景是否可实现以及是否确定的问题。
众所周知,科学早已超越了牛顿经典的确定性,经过量子力学的革命,以混沌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后现代的“不确定性”科学,已经在各个边缘领域发挥了作用。
以前,我们都相信某些尚未被证明的东西,如“物质无限可分”,或“物质不能无限可分”;如“天国”、“西方极乐世界”,或“共产主义社会”。
现在,这些信仰都变得不那么确定,它们与后现代科学的不确定性深深相容。
但是,总有一些人,他们能够接受对“天国”的向往,却不能容忍“共产主义”。
作者声明: 本专栏展示的文章皆为吴小萌原创,版权由作者所有,任何引用务必注明出处,任何构成抄袭的使用和未通过本人许可的使用,皆为侵权,违者必究。
注释: 该文章由作者赠稿,文章不代表本网站观点。